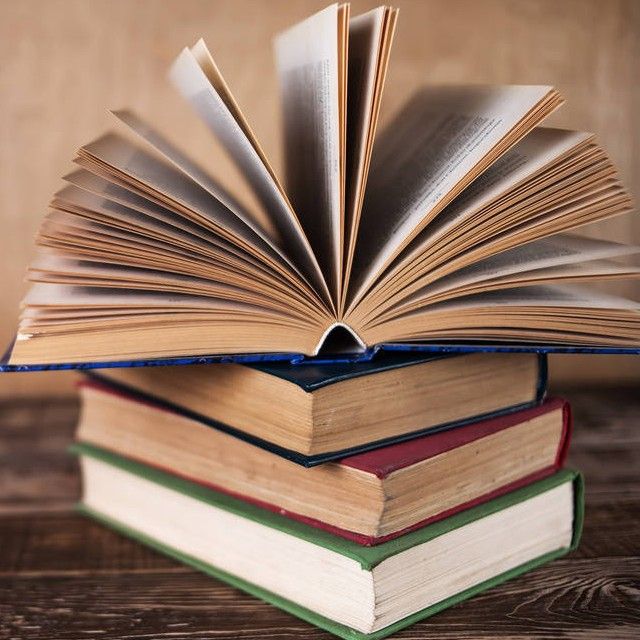1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对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希望读一读有关图书,思考这种影响的变迁与演进的模式与路径,以及可能对文化与文明产生的影响。在此之际,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在智库“新美国”召开的论坛上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来制定对华战略。这位黑皮肤的非裔美国人称:美国正在做准备与中国进行一场“文明与种族的较量”。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非高加索人种的强大竞争对手。”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前议长金里奇也声称美中冲突是长期的“文明冲突”。[1]
基伦·斯金纳关于中美之间因为处于不同的文明范式而注定要发生冲突甚至是战争的观点,主要源于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赛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亨氏的观点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自论文和图书出版以来,中国有关方面高度重视,不少专家已经发表了很多有份量的批驳文章。针对各方的观点,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文版的“序言”中辩解本意并非如此。他说:“我所希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
从文明的角度思考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并不完全是亨氏的独创,在西方社会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中,对于文明形态的认识,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却是渊源有自。德国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没落》,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亨氏这种文明冲突理论的源头。
2
其实,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最早是一篇论文,发表在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当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消失以后,国际上不再是国与国之间,或者是意识形态之间,或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冲突,国际间的冲突将代之以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他将世界上的文明分为七类:1、西方文明,2、中华文明,3、日本文明,4、伊斯兰文明,5、东正教文明,6、拉丁美洲文明,7、非洲文明(可能存在)。对于这七种文明,从内涵和外延上,他都给以了一定的界定。
关于中国文明,亨廷顿认为也可以叫中华文明、儒教文明。他认为,中华文明始于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追溯1000年,应是世界上最久远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超越了国家实体,也应当包括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还有越南、朝鲜的相关文化。他认为,在21世纪的未来的岁月里,主要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可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发起挑战并构成威胁。
关于西方文明,大约出现在公元700年到800年,分布于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什么是“西方文明”?亨廷顿在总结各类学者的观点后认为,包括:1、古典遗产。即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2、天主教和新教。3、欧洲语言。包括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5、法治。6、社会多元主义。7、代议机构。这种代议制在1000年前就已经实行。8、个人主义。从今天来看,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包括:三权分立、自由市场、人权、个人主义、法治。

新华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 版
亨廷顿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了回应人们对这篇文章的“误解和争论”,也为了进一步阐述他提出的问题,亨廷顿在论文的基础上“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形成了系统的阐述其理论观点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它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与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等。此书1996年由美国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随即翻译了22种文字。中国新华出版社于1998年引进出版了中文简体字版,亨廷顿为中文版专门写了篇“序言”。我现在读到的是新华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的版本,书名已简称为《文明的冲突》,由周琪、刘绯等翻译。出版者在“编后记”中说,这一版“在以前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修订,重新推敲译名,订正若干译文”。并将潘忠岐和李慎之先生的两篇介绍和评述亨廷顿此书的文章附在书后。
3
将人类的文明分为几种甚至几十种类型,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来看,1918年斯宾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却是这方面的先驱之一。
斯宾格勒全名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柏林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一个人隐居在伦敦的贫民窟里,开始了宏大的写作计划。这是1912年,正是一战爆发的前夕。六年后,《西方的没落》带着一战的创伤与反省出现在德国的书店里,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此书在民国期间虽然在汉语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一直没有全部译介到中国。1963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该书的第二卷,1986年,台湾远流公司出版了它的缩译本,1997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其全译本。目前,国内有译林等上十家出版社又重新翻译出版了这本西方学术经典。

北京出版社2008年9月第1 版
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以生物生长过程的观念进行历史研究,把世界历史分成八个完全按照自我的轨迹发展的文化,细致考察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现象,揭示其共同具有的产生、发展、衰亡及其毁灭的过程。斯宾格勒对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革新,他对每一种文化的现象采取“观相式”的直觉把握,以某些基本象征来揭示这种文化的全貌,他称之为“文化的形态学”。
《西方的没落》出版后,汤因比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我读着这些充满历史洞见性的文章之时,我开始产生这样的怀疑:我所要探讨的问题在被提出之前,就早已被斯宾格勒处理过了。”
不过,汤因比不知是否受到斯宾格勒的启发,还是他自己早就打算对历史的发展、人类文明的演进有自己的思考。这位同是因为生病没有到一战战场上去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教上古史的历史学家,开始了他的12卷本煌煌巨著的写作。他从1927年开始写作第1卷,到1961年写完最后1卷《历史的反思》。因为卷帙浩繁,一般的读者很难读完,历史学家索麦维尔先生将12卷本节缩到3卷。节缩本经汤因比先生审阅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上卷和中卷中文简体字版于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1966年6月又出版了第2版。下卷1964年才出版,我读到的是收入“西方学术译丛”的版本,于1986年10月第3 次印刷。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汤因比将世界文明分为二十一个文明社会。它包括:西方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伊朗和阿拉伯社会又全称为伊斯兰社会)、印度社会、远东社会、古代希腊社会、叙利亚社会、古代印度社会、古代中国社会、米诺斯社会、印度河流域文化、苏末社会、赫梯社会、巴比伦社会、埃及社会、安第斯社会、墨西哥社会、尤卡坦社会和玛雅社会。在目前的二十个社会中,也还可以把拜占庭东正教与俄罗斯东正教分开,把远东社会分为中国社会和朝鲜-日本社会。他还认为,古代中国文明以前的商代文化,可以分为一个独立的文明社会。
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7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4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8月第1 版
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亨廷顿,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对人类文明的研究上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首先,他们都认为人类的社会已进入了文明的阶段。文明这个概念,从18世纪法国的学者提出以来,学术界已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文明的标志要具有城市、铁器和文字,否则是“野蛮社会”。但对于文明这个概念,历史学家们还在用自己的解释丰富其内涵。在斯宾格勒那里,他认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文明。而“文明”则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可悲的归宿”。汤因比认为文明是涵盖一切而不被其他事物涵盖的一个总体。在一定程度上,文明是社会的同义语。亨廷顿则认为“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它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2]
第二,他们都注重从宏观上对文明进行研究。从斯宾格勒开始,他们反对过去历史学家将文明割裂开来讨论的方法,认为文明的形态不是以国家和某个时代来决定,而是与历史和社会、人的发展紧密相关。施宾格勒反对将历史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他认为这一体系产生一些难堪的错误。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大文化的历史,而民族只是具有象征性的形式和容器”,“文化是通贯过去与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现象。”[3]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4]。亨廷顿则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5]

德国历史学家施宾格勒
第三,他们都认为文化、文明是多元的。针对叔本华、费尔巴哈、尼采等人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论”,他们认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种文化在不同的地域生长、发展,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斯宾格勒认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如教堂“无限的空间”,建筑耸入云霄,好似伸向无垠的天穹;阿拉伯文化是“洞穴”,中国是“道”。因此,他将世界上的主要文化(文明)分为八类。它们是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汤因比也反对文明的河流只有西方这一条的理论。他说:“已知的具有文明发展过程的社会迄今为止有二十一个。”他认为七个是母体,另外的十四个是子体。[6]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7]所以,亨廷顿将世界上的主要文明分为七个类型。
第四,人类历史上的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不同的宗教。无论是施宾格勒、汤因比,还是亨廷顿,都把宗教看成是区别不同文明之间的主要因素。亨廷顿认为:“在所有的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主要的通常是宗教。”[8]他也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文明的类型。如他认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教,所以又可称为儒教文明;印度文明主要由印度教为核心;伊斯兰文明主要是伊斯兰教;东正教文明的核心是东正教;西方文明主要是基督教。而日本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则是儒教和天主教的衍生。犹如汤因比所比喻的“母体”与“子体”的关系。
第五,他们都认为文明有一个发生、发展与衰落的过程。斯宾格勒看到,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壤中生长出来,都有一个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的过程。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和死亡五个发展阶段。不过,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不同的是,他并不认为某一种文明的死亡是必然的。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应对“挑战和应战”的能力。“是少数人的创造能力的衰退,多数人的相应的撤消了模仿的行为,以及继之而来的全社会团结的瓦解。”[9]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他在对文明进行比较时发现,他所概括的二十一个文明,其中有七个还活着,另外的十四个已经绝迹了。有些本来就属于“历史的黎明时期”的古代早期文明。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
第六,他们都对西方的文明表示了共同的忧虑。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亨廷顿,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未来都表现出忧虑。特别是斯宾格勒,面对迫在眉睫的一战,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与颓废,有着深刻的洞见。他将这本探究西方文化命运的历史哲学著作命名为《西方的没落》,足见其对西方文明未来结局的悲观。一战的残暴,经济的萧条,道德的沦丧,剧烈的社会矛盾,印证了斯宾格勒观点,因而一战后的人们对施宾格勒由不屑一顾到刮目相看。汤因比刚开始并不完全赞同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文明将要没落的观点。他虽然已经看到了西方社会“有衰落与解体的各种迹象,但他不愿做出论断。”[10]但到了晚年,汤因比认为西方“狭隘和傲慢”,存在着让世界围绕着西方在旋转的“错觉”。亨廷顿则认为西方文明“始于20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11]相对于其它文明而言,西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力量正在下降。“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12]他认为,西方文明无法做到与世隔绝,又不能一统天下,所以来自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巨大挑战,使西方文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同时,美国国内的种族矛盾,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挑战,多元化主义提倡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也在动摇以基督教为代表的以欧裔白人为主体的西方文明。
4
所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特别是在对文明的界定,文明的生长、发展与衰落上,都是把文明看成是一个具有自身生命特征的有机体。但亨廷顿在学术上的创新就是用文明这个视角来观察国际政治。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亨廷顿为理解下个世纪全球政治的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13]当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主地位”时,作为西方文明领头羊的美国,会感到难以接受。所以,他用一章的篇幅写到中美之间如何因为一个局部冲突引发为一场全面战争。
如何处理并采取“避免原则”,让不同文明之间不发生冲突,做到各种文明之间的包容与和平共处,亨廷顿没有开出药方,而是引用了20世纪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的警世名言:
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与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面,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
但是,话又回到前头,为什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在中美经贸战愈演愈烈之时提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将是一场文明的冲突呢?是亨廷顿不幸而言中,还是亨廷顿的预测与推演提醒了美国的政策制订者?
参考文献
[1]郑汉根.新华社.http://www.crntt.com/crn-webapp/doc/docDetailCNML.jsp?coluid=7&docid=105425347
[2](美)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7
[3](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北京出版社,2008
[4](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4
[5](美)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4-28
[6](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58
[7](美)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5
[8](美)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6
[9](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56
[10](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457
[11](美)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356
[12](美)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78
[13](美)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438
作者简介

周百义 出版人、作家。曾任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长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现主持编纂出版1600册《荆楚文库》大型文化丛书。主持策划的有《二月河文集》《历史小说大系》《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新时期报告文学大系》等。责任编辑系列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张居正》等。本人写作并结集出版的有:小说集《竹溪上的笋叶船》《山野的呼唤》《黑月亮》,历史小说《她从魔窟来》(与人合作),报告文学《步履艰难的中国》《中国反黑行动》(与人合作),古籍整理《五经七书译注》《白话劝忍百箴》《预知.预兆.预见》,出版研究专著《出版的文化守望》《书旅留痕》《书业行知录》等。有《周百义文存》3卷。最新出版的有江西高校出版社《长江十年》一书。
免责声明
本文为“荆楚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荆楚网提供信息发布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