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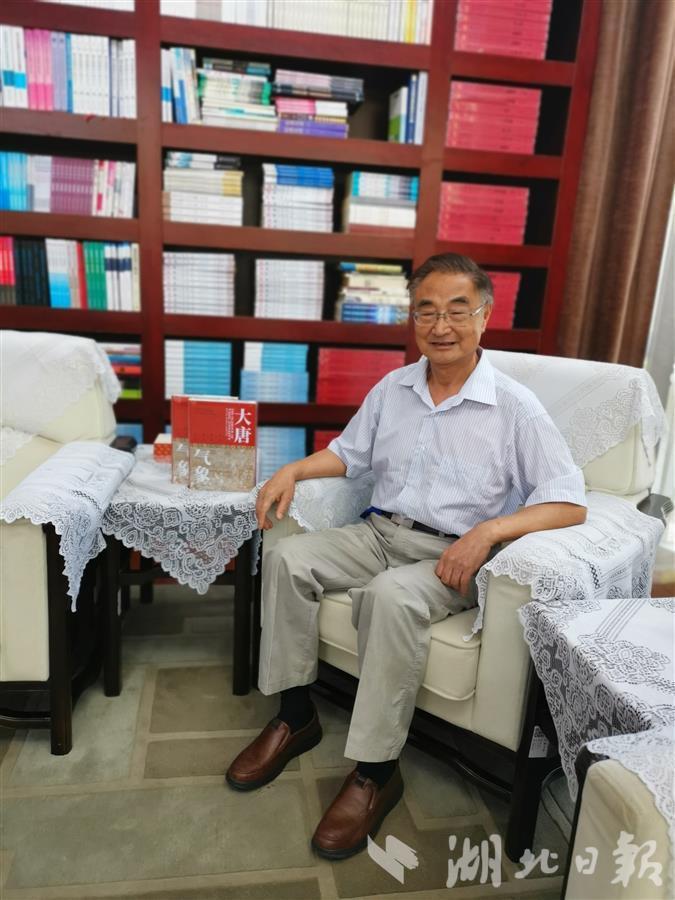
7月30日,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望衡,走上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主讲《唐朝:世界文化史上的光辉旗帜》。
陈望衡、范明华等合著的《大唐气象:唐代审美意识研究》(以下简称《大唐气象》)于年初出版,引发学界及公众高度关注。《大唐气象》从唐诗说起,但不就诗言诗,而是构筑了大唐文化与其朝代建制、社会语境等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基础相匹配、相适应的整体“景观”。有评论认为,书中的气象,是滥觞于诗歌而散延于其他领域的血肉、气韵、格力、体面、情致和意境等总体性的审美风貌,更是一个时代整体的精神面貌,书中所及的音乐、书法、舞蹈、服饰等,均折射出唐代美学恢弘宽远的意蕴和风骨。
在长江讲坛两个小时的讲授中,陈望衡教授主要以唐诗为眺望大唐的窗口,他3次强调,“要多读唐诗,唐诗读多了,读懂了,境界就会不一样了。”
我爱大唐青春美
陈望衡教授在长江讲坛开宗明义:“我喜爱推崇大唐,是因为我的审美观是青春审美。”陈望衡说,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假如用人的一生来比喻,那唐相当于青年,宋则为中年。青年有旺盛的生命力,勇于探索。青春的形象也许有几分粗糙,几分鲁莽,几分幼稚,但它可爱,可爱压百拙。
“一说起唐,我眼前出现的影像就是朝霞满天、崇山峻岭、汪洋大海,还有充满活力的少年男女,是青春,是壮丽。”
陈望衡表示,唐朝实施开放的国策,是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是世界贸易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唐代人的信心满满与豪情万丈,我们从唐代的诗歌、乐舞、绘画、书法、雕塑中都能体会见识到,“青春,是活力问题,而非年龄问题,唐代的审美品格就是青春美学。”
对于时下一些年轻人的“躺平”,陈望衡不认同:“青春,源起于年龄,但其内核不是年龄决定的,青春的核心是上进,人生有追求。看唐人诗歌、音乐、书法,其间的信心与豪情、自由与追寻,是当代人所需要的。”

唐诗里的乐观气概、劲爽境界
陈望衡在长江讲坛与读者分享,唐人心态总体上可以用“乐观进取”来概括。我们可以从唐朝文化的标志之一唐诗来观察体会。
“唐朝诗人不少屡遭贬谪,但总的来说,不颓丧,不悲观,不消极。刘禹锡是其中代表,他在贬谪途中赋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心态跃然纸上。他有《秋词二首》其一云:‘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种将诗情引到碧霄的心态,是唐人共同的心态,这种心态极具唐朝的特征,它只属于唐人。唐人极少言失败,更不言绝望。晚唐帝国风雨飘摇,诗人杜牧在《题乌江亭》一诗中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唐诗中青春审美还体现在劲爽境界。陈望衡举例:“比如率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倾耳为我听’;比如轻快,‘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比如清新,‘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岸夹明镜,双桥落彩虹’;比如流美,‘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唐诗,更多的是赞叹,是鼓舞,是自豪,是自信。”陈望衡说,“李白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高适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即使面对强虏,唐朝将士也信心满满:‘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
边塞诗展现唐朝的国魂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 “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在这些脍炙人口的豪迈诗篇里,“我们能体会到唐帝国的时代精神:踩着瓦砾,踩着尸骸,雄强奋发,呼啸前进。”陈望衡表示,唐诗中的精华是边塞诗,主题是家国情怀与功名情怀,以崇高壮丽为品位。
陈望衡说:“边塞诗所反映的战争情感有深刻的内涵,正义的战争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崇高之美。唐朝边塞诗唱诵的是唐朝的国魂。”
讲座结束后,陈望衡为长江讲坛题字:“大唐魂犹在,高歌向未来”。陈望衡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统一体的中华民族真正形成是在唐朝。中国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国美学成为中华美学,始于炎黄时代,成于大唐。边塞诗、敦煌艺术、《霓裳羽衣曲》等都是中华艺术的最早代表。对唐代审美意识进行研究,是一个认识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了解当下的审美意识是怎么来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对树立文化自信有重要意义。只有不忘来路,才能想明白自己有着怎样的使命和去向。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