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日新先生在大冶特钢厂 罗日新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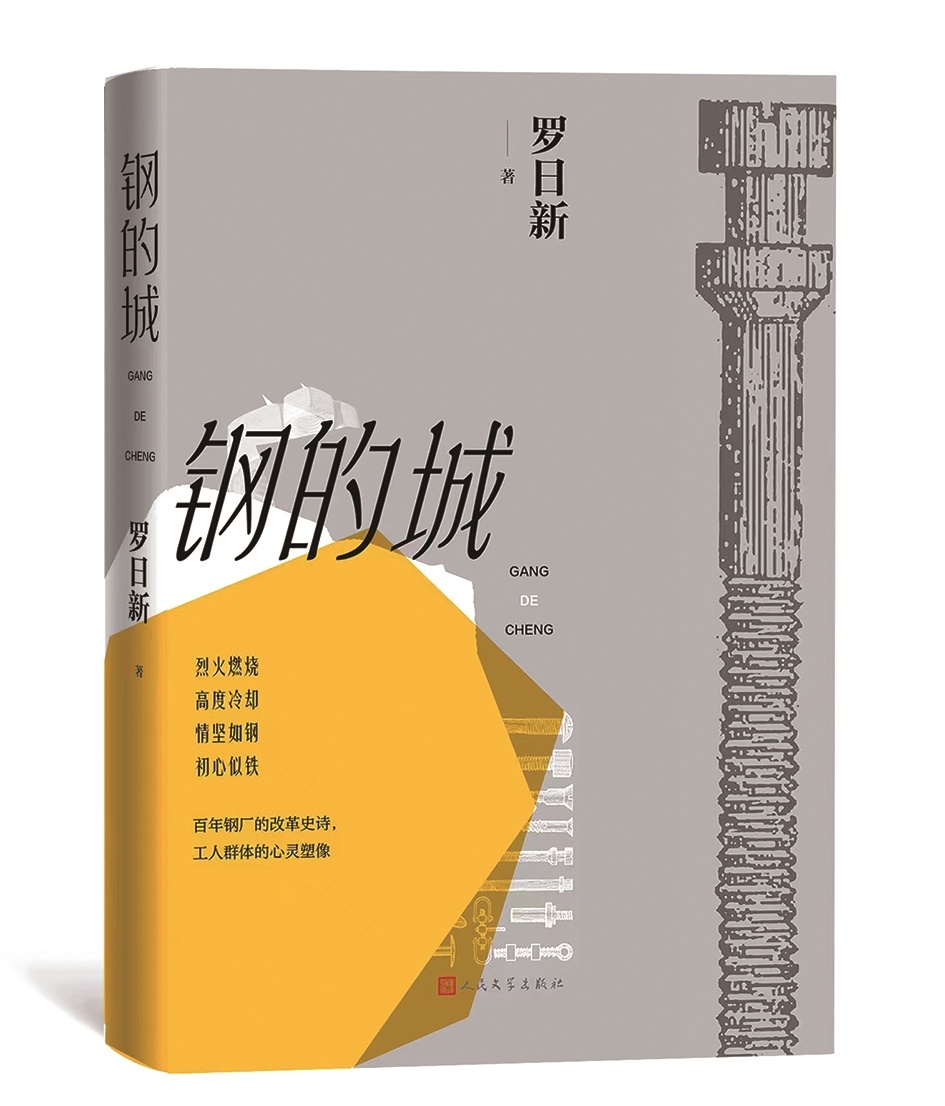
《钢的城》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樊星
与名作多多的乡土文学相比,工业题材文学的成就显然单薄了许多。虽然也有左拉的《萌芽》、科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弟》、黑利的《汽车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那样的经典作品为人称道,可“工业题材作品为什么不好写”一直是一个人们有点困惑的话题。连都市文学中也多见《骆驼祥子》《长恨歌》那样写市民生活,而不是工厂生活的作品。因此,从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产生的轰动效应,到1996年谈歌的《大厂》为工厂转型遭遇的困境发出的深长叹息,还有同年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以及2002年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2004年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因为聚焦下岗工人的命运而引人注目,都体现了当代文艺家挑战难题的可贵努力。是呀,与当年大规模“下岗潮”并存的,有没有企业和工人生活的另一面?如中国制造的产品逐渐走向世界,中国的企业家也迅速成名——像民营企业家鲁冠球、曹德旺等等,还有那些一鸣惊人的优秀工匠、劳动模范……他们是如何过关斩将、身怀绝技、一举成名的?已经有不少纪实文学写出了他们的生活、个性与命运。
最近,湖北黄石作家罗日新的长篇小说《钢的城》(第一、二部)一经发表,赢得好评如潮,就因为这部小说为民营企业的突围、崛起谱写了一曲五味俱全的“正气歌”。是的,一说到“正气歌”,很容易使人想到或悲壮、或高亢的旋律。而在生活中,其实是有五味俱全的“正气歌”的。
我注意到,罗日新曾经不止一次谈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他的深刻影响。那是一部影响过两代青年的红色经典。当代不少上了年纪的作家都曾经一往情深地回忆过那本书的感染力。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那本书激励过许多热血青年的奋斗。到了世俗化年代里,那本书的意义就止于怀旧么?其实不尽然。保尔·柯察金的艰苦奋斗精神不也是人类自强不息精神的延伸么?而罗日新本人在大变动的年代里与时俱进、成为商海中的弄潮儿的经历,以及他谈起在国企勤勤恳恳、尽职尽责,下海以后奋力打拼、不断进取时的满腔热情,都充满了令人感动的“正能量”。这样的“正能量”一直是许多创业者的力量源泉。甚至,即使在告别了体制以后,他笔下的祝大昌仍然一往情深地谈到从“大厂”中走向竞争激流的人们“聚是一把火,散是满天星”的适应力,足以使人想到许许多多通过奋斗成为了新生活的主人的人们。那是与“下岗潮”并行的另一股潮流——“创业潮”。
在小说主人公祝大昌的身上,可以使人看到罗日新本人的影子:一面锐意进取,一面不能不面对政策的限制,一面还得在美国“反倾销”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挤压下想办法突围;一面又因为弟弟的投资败笔、母亲的偏爱与误解、妻子的不解而尽力应对、耐心周旋,还有自身的积劳成疾……正是这样的重重压力,才真切写出了民营企业家打拼的不易,写出了许多企业家的共同生命体验。这是与当年的乔厂长大刀阔斧搞改革很不一样的生存环境了。是在国际、国内竞争日益激烈下承受多方面压力,使出浑身解数、调动各种力量,去上下求索、左冲右突的心路历程。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样,这部小说就有了理想主义的色调。
这理想色调,是在世俗化年代里,既保持了进取心、又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多谋善断的基础上,显出稳扎稳打的实干品格。这样的品格,一直没有因为虚无主义浪潮的冲击、各种牢骚的干扰,还有现实难题中各种麻烦的纠缠而消失过。写好这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写好这种实干家的矢志不渝的坚定品格、从容应对的平常心、以及在长期拼搏中积累起来人脉实力,是这本书的一大看点。如果说,当年,《乔厂长上任记》写出了改革的艰难,英雄气中透出悲凉,那么,《钢的城》则写出了突围的不易,在一心一意谋生存、谋发展中凸显民营企业家的处变不惊、多谋善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这也正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相通的处世秘诀吧!
所以,《钢的城》写出了当今生活的一大特质:一边是国际关系的大变动、加上疫情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瞬息多变,史无前例,惊心动魄;另一边,则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虽常常有波澜,却也在各种力量的互动、协调下得以化解、平息。生活不仅仅是一地鸡毛,也有各种涌动的暗流和许多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在不断抵消着生活中的“负能量”。写出了这样丰富的层次,就写出了生活的五味俱全、人心的深邃博大。都说这是个“内卷”的时代,同时,不是也常有各种创业的传奇在传扬吗?创业需要机遇,需要资金,需要人脉,还需要坚定的意志、博大的情怀。《钢的城》就这样写出了人生的哲理底蕴,令人不禁想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加缪的《鼠疫》、张承志的《金牧场》……那些读来感到既沉重、也感伤、还振奋的好作品。
从这个角度看,《钢的城》也打开了工业题材出彩的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