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极目新闻记者 夏雨

对话背景:
9月11日晚,充满湖北腔调、武汉元素的红色曲艺剧《三教街四十一号》在武汉剧院亮相。中国曲协主席姜昆受湖北省文联之邀观看演出,与近千名江城观众一起“穿越”到1927年的老武汉。
武汉,对姜昆来说并不陌生,这里有他横跨40年的曲艺情缘,甚至还有一场直面死亡的难忘经历。
9月12日,在姜昆下榻的酒店,可以看到江景的窗边,极目新闻记者独家专访了他。窗外,船舶缓缓前行;窗内,姜昆将他的曲艺故事娓娓道来。面对如浪潮般涌现的文艺年轻人,他说,他们须在前行途中,点亮四盏“明灯”。
人物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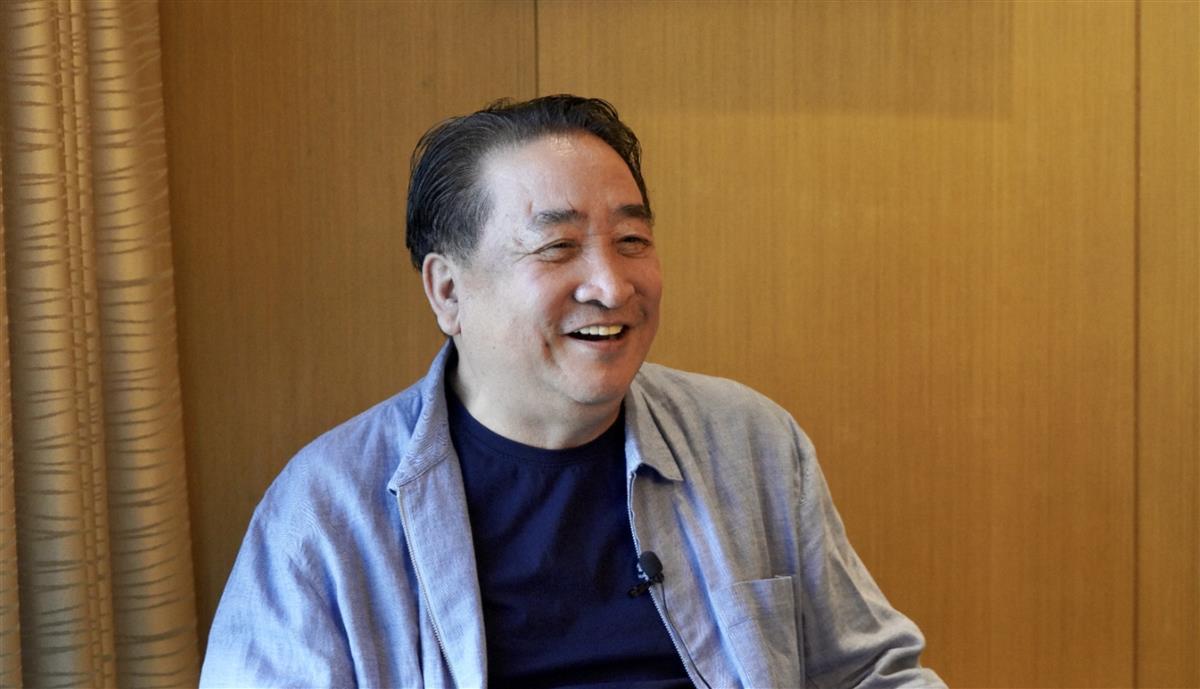
姜昆,中国曲艺、相声事业的领军人物,现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他从艺50年,勤奋敬业,功勋卓著。创作表演了《如此照相》《虎口遐想》等上百段相声作品。CCTV央视春晚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团长、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中国曲协党组书记、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等职务。
谈湖北情缘
大概年轻人都没听过这些名字吧?
极目新闻:因为湖北曲艺“百花书会”,2018年您去到了襄阳,今天您再次来到湖北,我们都很高兴。
姜昆:我经常来湖北,实际上,我前不久还去了恩施、宜昌,因为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广泛开展了“送欢笑下基层”的演出。这次来武汉不止是为今年的“百花书会”,也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文艺志愿者在这儿举行比较大的活动,而我提前两天就到武汉了。
湖北的曲艺历史其实很深,就拿咱们北方的相声来讲,过去这里有侯宝林先生一个弟子,也就是我的师叔辈,叫胡必达,还有一位老前辈是跟夏雨田老师一起合作的杨松林老师。大概年轻人都没听过这些名字吧?但他们都是我们中国相声界里边可圈可点的人物。
现在我很关心我们的武汉说唱团,因为这里有我的四个徒弟:陆鸣、许勇、李道南,还有赵卫国。说到收徒,还要感谢夏雨田老师。
夏雨田老师是我们中国相声界一个极特殊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是相声界第一个大学毕业生,有知识有文化,又是我们中国相声界在当时唯一一个有比较高的公务员职位的人,曾任武汉市宣传部副部长、武汉市说唱团团长。大概1982年前后,他把这4个学生嘱托给我,说“你一定要收,要帮助我们武汉,让北方的相声在这扎根。”现在他们也是湖北曲艺的中坚力量。
我因为和夏雨田老师合作,熟悉了很多当时在我们湖北这块大地上的优秀的曲艺家,比如张明智老师。我一遍一遍听他的湖北大鼓,从一点听不懂到听得懂一半,到最后他一唱,我就能和了。
曲艺剧《三教界四十一号》里的湖北方言,我百分之九十能听懂,跟听湖北的曲艺有一定关系。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也受到了何祚欢老师的方言评书、何中华老师的大鼓演唱的艺术熏陶。所以我不管是到黄石黄陂,还是到宜昌荆州,我一定要听当地的曲艺,也会带那里的曲艺人出来,去参加全国的曲艺比赛,进行交流。
谈艺德行风
我们为什么在那次特大洪水下坚持下来了?
极目新闻:面对近期文娱领域的违法违规、失德失范现象,8月24日,中国文联发布《修身守正 立心铸魂——致广大文艺工作者倡议书》。我们湖北省文联也迅速响应,全面加强湖北文艺界职业道德和行风建设。您作为中国曲协主席、中国曲协行风建设委员会主任,您觉得曲艺人应该怎么做?
姜昆:我还是从湖北说起。1998年,湖北发特大洪水,因为关卡太多,也太危险,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当时都没有进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亲自指挥这样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洪行动。当时我们都特别想到现场,我有幸获得一次机会。
中央电视台的领导同志突然有一个想法:让姜昆去湖北,他在那生活过,那张脸就是“通行证”。于是我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鞠萍结伴而行。8天时间,我每一天都在堤坝上,除了帮助电视台进行一些采访外,也和鞠萍一同演出,给大家唱黄梅戏,唱各种各样的歌,鼓舞人心。
但我多少有点恐惧,放眼望去没有村庄人家,只是一片汪洋,水面上能看见的只有冒出来的深色的树梢,雨,永远不停地下……当时我有一个念头:如果说有一个地方破了的话,那我脚下几十公里也会成为汪洋。
现在我回想起来,就想,如果今天让我们的一些明星们在前面走着,保安后边跟着,助理保姆在两边护着,能完成这个任务吗?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上待上8天,他们能坚持下来吗?我打一个问号。可是那时候我们为什么坚持下来了?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文艺人风清气正。
中国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其实有一个传统:我们的事业,跟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那是血和肉的关系!
今天的这些年轻人偏离了这个方向,这个关系没了,他们跟天价的报酬是血和肉的关系……
这一次,我就提出了,艺术家尤其是年轻人的眼前要有4盏灯:第一盏是方向,如果专门去认钱,这道就走完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第二盏是标准: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是人民的灵魂工程师。我们每个人都要想想,你是做一个灵魂工程师,还是市场的奴隶。第三盏,是责任。不单对我们这一代负责,你是不是应该对下一代负责?我跟相声演员说,你们的节目演给周围的朋友听,一帮女粉丝们哈哈大笑,你们再想一想,这样的节目能不能给孩子听?我们是公众人物,一半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社会。最后一盏就是底线。文化艺术工作者要守住底线,不踏红线。有一些红线是看得见的,吸毒、失德、失范,完了以后甚至刑事犯罪。有些底线是看不见的,例如你宣传一些低俗的、庸俗的,甚至是隐晦的、暧昧的、打擦边球的东西。
谈包袱创新
没有生活能写得出这样的话吗?
极目新闻:有张黑白照片令人印象深刻,那是1977年,在北京开往呼和浩特列车上的相声表演,马季先生逗哏,您捧哏。围观的人无不开怀大笑,十分明媚。这样的画面我们似乎难再见。
姜昆:马季老师长期以来在火车上给人演出,这是家常便饭,所以他拉着我,“走,咱们去给人家说段相声去!”我们走到哪儿演到哪儿。我留了很多马季老师带着我深入生活的照片,有带着我们到农村农户家里边的照片,在工厂里边参观劳动的照片,跟人家职工打篮球的照片。那个时候,我们的演员基本上是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的,不像现在的年轻偶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能写出各种各样的作品,因为素材来源于生活,来源于老百姓身边。
极目新闻:您能不能回忆一下,您通过深入生活获取到的灵感。
姜昆:我原来跟李文华老师搭档,李老师家住和平里,104无轨车终点站,我每次都坐这路车去找李老师商量节目。有一次我们到车站附近的工厂找工人聊天,后来工厂工会一听李文华老师来了,就召集了好多工友来分享各式各样的,发生在104路汽车上的笑话。后来我们就创作了《我与乘客》。
我给你讲讲开头几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跟我们老何同志呀在一起,跟大家说段……”“诶诶诶,您先别说了,还没弄清,我不姓何。”“您看我这记性,他姓平,我们那老平同志啊……”“等等等,我不姓平。”“那您姓什么?”“我姓李!”“哦,和平里(李)……”“我还北京站呢!”“和平里、北京站、104…… ”“嗯,大无轨。”“大无轨(大乌龟)同志您好……”
你听听,这样的话,没有生活能写得出来吗?
极目新闻:《我与乘客》这个作品里,您还说了东北话。您是第一个用东北话讲相声的人。
姜昆:我在东北生活了8年,我把那些嘎子壳,就是土话,融进去做成了包袱。比如,“前两天坐车,看一外宾进大会堂,我问他外宾去干啥,他说外宾去会餐,我问外宾吃啥,他说猪肉炖粉条,外宾可劲儿造……”“你就是高山上点灯,就那一嘎达”“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不起我们外地人,你被窝里伸脚丫子,你是第几把手?”那是1978年的事情了,后来都司空见惯了。
极目新闻:这样的包袱,现在就叫梗了,您刚说的“和平里”,就是现在很火的“谐音梗”,原来四十年前姜昆老师就“玩过”了。那现在,我们的曲艺创作,该怎么去创造新的包袱呢?现在对于曲艺人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
姜昆:从创作方面来说,年轻人还是懒惰了。现在互联网上面各种各样的笑料、你们说的梗太多了,他们就信手拈来,完了以后取一时之欢笑。这些东西就是拿来主义,它不是经过你深入生活,严肃地构思,刻苦编写而成的。一定要有长期的语言积累,然后偶然得之,灵感一出来用在上面,艺术效果才出得来。
创新还是要深入生活,并往深了写。因为相声是一种“搞笑”的艺术,笑是荒诞、夸张,它是基于生活的夸张,越荒诞越蕴含哲理。笑有的时候是可以很简单的,是吧?很简单的就是能够让大家发笑,但是笑,还得有滋有味。
至于时代,我觉得,现在社会各界对演艺界行业风气的高度关注,国家主管部门重拳整治整个饭圈乱象,这种时候对年轻来说是个契机,就看谁跑到前面,重新思考一下身子上的责任,重新寻找道路的方向。年轻人要摒弃那些投机取巧、哗众取宠,懒惰的做法,还需耐住一点寂寞,塌下心来向老艺术家学习,从经典中寻找、摸索,然后,便是大显身手的好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