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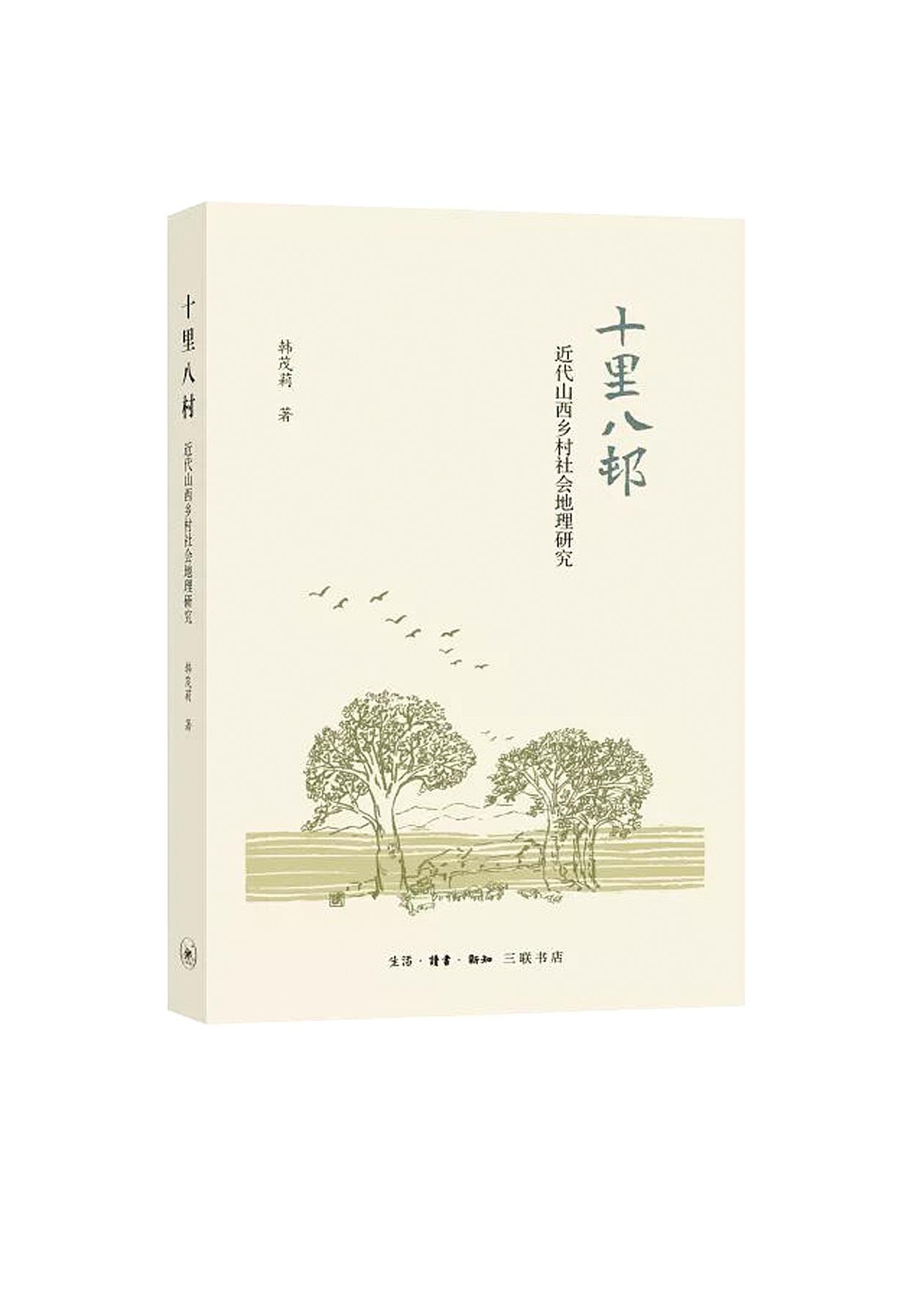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李茜 谢宁
“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是我们常听到或说起的一句话,“十里”“八村”这样的概数,背后有没有社会现实的支撑?为什么不是三里、二十里、五村、十五村?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韩茂莉著作《十里八村——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以近代山西作为研究样本,不仅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框架与学术体系,而且在理论上实现了重要突破,揭示了乡村社会规律性的地理特征,揭秘传统中国农民直接认知世界的空间基础。
5月15日,韩茂莉教授走上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讲授公众认知中熟知又陌生的“十里八村”,并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
乡村社会地理:围绕农民生活、生产的空间概括与理性分析
记者:您在讲座之初,展示了一幅示意图,绳子一端拴着石头,一端握在人手,手摇动绳子,形成一个圆周运动。无论这个运动的速度有多快,石头永远以人手为中心,石头运动最远距离的半径就是绳子的长度。这幅示意图对我们理解乡村社会地理的研究范畴、研究对象有什么帮助?
韩茂莉:我研究的对象历史背景是传统农业社会。中国是农业大国,我们进入工业化进程,脱离传统农业时代,最早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70年代,即便到了今天,传统农业的烙印仍然在我们生活之中。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以及围绕土地的农业生产构成隐形的吸引力,决定着村民一切空间行为的范围与尺度。在石头的圆周运动中,有一种内在的束缚力,这种束缚力把运动限定在一定空间范围。在传统农业活动之中,土地就是这种束缚力,也就是限定性的空间范围。
乡村社会地理,是农民在生活和生产之中形成的一种空间规律。既然有规律,一定会有一种内在的因素驱使、导致或者约束。传统农业社会,农民耕作的对象——土地,就是这种内在约束力,以土地为生产对象的农民,他们所参与的生活、生产乃至于社会活动,都是以土地为核心的。
记者:借由您的调查研究,我们看到山西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晋泉县、太谷县等农村农户的经营类型、耕地面积、耕地距村落的距离等,共同构成了当年的农村社会的某些侧面。
韩茂莉:这些资料可以向我们展示乡村农民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农业立足土地,农民从事生产、建立村落,土地作为农业生产依托的根本资源,不仅令农民依附于土地之上,且土地的不动性决定着农民认知世界范围的有限性。尽管山西乡间农民可分为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及佃户、工农,但农民的职业属性没有根本区别,这些依附土地生产的农民不仅安土重迁,且主要生产空间保持在以村落为核心、以耕地为半径的范围内。
农户是乡村社会成员的主体,农户中占80%左右的自耕农、半自耕农对于土地的附着性,成为乡间认知空间的决定性力量,不仅将乡村生活控制在农业生产的范围之内,且具备时、空双重稳定的特性。
研究样本我们发现一个事实:所有在历史时期留下一家一户土地分布及面积记录的,几乎没有一家人的土地是完整连成一片面的。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农民在家庭发展的过程之中,土地是在产业逐渐增值的过程中,不断购置的。不断购置的土地往往分布在不同的位置。另一种情况,一个大家族,儿子成年之后要分家,分配祖上的土地会“肥瘦搭配”,也导致东南西北村落各个方向都有土地。
这些零碎分布的土地,究竟距离村落有多远呢?我们的调查中,2里以内占绝大多数,极少数的在5里左右。这是山西的情况,在中国南方,农民从家门口到自己耕地距离会更短一些。
从村落到耕地的这段距离,就是农民的生产空间,这个生产空间有一个基本保证:从村子走到地头,完成一天的生产活动,保证晚间回到自己的家中。从炕头到田头,这是农民生产空间距离,由于土地不动产的性质,这就是限制农民认知空间的一个主导的因素。
记者:农户散落在村庄各处,村庄散落在山河间,国家机器是怎样把一家一户的农民管理起来,让他们交粮纳税?
韩茂莉:道光《直隶霍州志》记载:“编里以统村,因村以立甲……每里立甲,每甲设立总户头,催办地粮等项。每村仍分设小甲一名或二名,管理地方公事、纠察奸匿,随时投报州县。”嘉庆《灵石县志》记载:“一邑之内村居比栉,垄亩同沟,往来皆熟识之人,交易亦邻里之近,耕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游则党使相救、乡使相宾。”
我们翻查光绪年《续修曲沃县志》所载该县里及里属村庄,曲沃县有38个里,每个里管理3个至11个村庄,距离县城最远65里地。光绪年间绛县共4个乡、26个里,距离县城最远60里地。这些乡间基层组织所领村落散布在30里以内甚至10里左右属于常态。
村这一自然形成的聚落在乡间始终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村落是村民生活的核心,以村民为管理对象的基层组织,将哪些村落纳入一个乡里组织,所要考虑的自然是村民之间的来往与熟悉程度,这样的考虑几乎包含在乡里组织所属空间的社会选择与自然选择之中。
乡村基层组织具有管理乡民的职能,而基层组织构成与管理形式的基础则是乡民的交往空间。山西乡村管理形式可分类行政管理与民间管理两类,但这两类基层组织的管理空间与管理者具有相通之处,即有效管理空间多在10里范围之内,而管理者则出自乡间的大姓且拥有财、能的实力雄厚者。管理空间反映的是乡民的基本交往范围,管理者的出身则再次将认知空间锁定在本乡本土。
记者:您所说的乡村基层组织,管理者的角色是否与费孝通先生所讲传统乡村治理的长老一致?
韩茂莉:中国古代任命官员最低级别通常至县一级,县以下乡村的管理者不属于朝廷命官,乡间管理者是乡村精英,也就是费孝通说所的长老。这些人非能即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自然拥有支配乡里的权威,获得这份权威的途径在于“预付资本”,“预付资本”不仅有物力、人力,还有贡献。
山西是缺水的,当地有“油锅取钱”分水的传说。几个村子一起修水渠,各村用水量如何决定?滚油锅放10个铜钱,某村年轻人下手捞出7个,这人手废了,但他的村子取得70%的用水量。传说真不真不知道,这个传说会被某个姓氏作为长久管理这个村子的一个条件。
长老还会怎样产生呢?比如南方很多省都有移民进入,一姓家族进入到一个地区,于是这个家族的长辈会变成整个同姓家族的族长,家族势力、宗族势力都具有长老的特征。
“预付资本”之中还有一种豪强特征的性格,比如刘邦,他没有什么财力,但是能打。各个村落之间发生械斗之时,冲在前面为本村出力的人,也有可能拥有长老身份。
传统社会农民认知空间的三个圈层
记者:在您的研究中,传统农业社会农民是怎样因空间而认知社会的?
韩茂莉:传统社会农民直接认知空间可分为三个圈层:第一为本村,这是以家庭为核心,以村落为依托的生活圈;第二为农田,以最远耕作距离为半径构成生产圈;第三为社交,村民的社交活动主要有前往集市的商品交易、婚姻、祭祀几种形式,其中通过集市交易构成的社会交往范围奠定了所有其他活动的基础,其他活动建立的空间关系大多叠加在集市交易范围之上,这一圈层为社交圈。
从“炕头”到“地头”仅是村民直接认知空间的第一、第二个圈层从属的范围,但这是乡村生活的核心。
记者:您研究的核心问题“十里八村”有一个切入点就是集市,乡村社会地理的视野里,集市是怎样的存在?
韩茂莉:乡村集市产生于农业社会之中,从形成到发展,均带有鲜明的农业生产痕迹。农业与商业属于两个经济部门,将农业生产的特征带入商品交易中的是依托土地而生存的农民,农业的丰盈决定地区经济进程以及剩余农产品的多少,进而影响村民交易需求的力度;土地的不动产特点则限制了村民的出行距离,需求与局限两者的结合,构建了乡村集市分布的地理格局。
近代山西,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村民对于商品交易的需求并不迫切,无论定期市集期间隔与客源区范围,还是集市呈现的整体地理格局,均属于商品交易处于较低阶段的产物。
“崇本抑末”的传统,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且将商品交易力度降低到最低水准,对于乡村尤其如此。乡村不但缺乏固定的交易场所,且无力维持日日交易的常日市场,定期市成为乡村集市的主要类型。
定期市指一月之内按照固定日期安排集期,以及相隔数日为周期从事交易活动的集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集市门槛值依托的范围较小,集市密度大,集市间距离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方,集市门槛值依托的范围较大,集市密度小,集市间距离远。
集期表面上是集市交易的间隔时段,决定集期的真正原因则是彼此间的势力范围,即客源区。相邻集市集期不同,说明它们处于共同客源区之内,同一批村民利用集期的差异,参与几个集市的交易活动;集期相同的集市,参与交易者几乎完全不同,他们分别处于各自的客源区之内。集期关联到空间,集期的变化也必然与客源区相关,定期市集期间隔缩短与增长与集市交易状态相关,集期间隔不变,而交易日期更动,则意味着客源区重新调整与市场资源的再分配。因此,一定意义上看,集期体现的是空间,且是由交易者行为而决定的空间。
传统农业社会,村民不仅在集市上完成交易,且将这里作为与周邻十里八村进行社交的重要场合,因此兼具买卖、社交乃至于娱乐的乡村集市,对于村民而言,意义远远超出交易本身。
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山西,推动集市形成的主力为农民与商人,农民既是集市物品的买方,也兼具卖方身份,而职业商人的服务对象则以当地农民为主,兼及与来自不同地带的商人互通有无。正是这样的原因,集市经营品以农产品与乡村日用品为主,由于中国乡村百姓日用消费大多处于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状态,因此集市上的商品档次多为当地农户日常需求的寻常之物,故集市与集市之间虽然存在集期间隔与规模的差异,但以交易品而论则不存在明显的等级与服务职能之别,即集市与集市地位平等,正是这样的原因,农民所有的交易活动几乎均在距离最近的集市服务范围内完成,这一范围基本在一日往返距离之内,超过这一距离的其他集市轻易不会光顾。
记者:您提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写的《朱陈村》一诗“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白居易写的是唐代村落,但在您的研究样本中,近代山西农村的婚姻依然是诗中所描述的状态。
韩茂莉:乡间农民生活的核心仍是家庭,活动的空间依然以村落为主,基本社交圈为近邻与血缘家族,婚姻则是走出近邻与家族,将社交圈伸向更远的基本途径。
由婚姻建立的社会交往空间与里甲制度不同,依托里甲建立的管理体系为被动加于村落与家庭之上的基层组织,而婚姻则是在主动求索中营建的交往空间,前者服务于管理,隶属于同一个里甲的多为邻近的村落;后者则依托亲朋与媒人的关系,将婚嫁范围伸出里甲之外。
白居易诗中的“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生者不远别,嫁娶先近邻”尽管是唐代的乡村生活,但在近代的山西农村依然如此。我的研究调取了大量的家谱,从中抽取了当地村民的婚姻状况,比如沁县道兴村张氏的联姻地、闻喜县西村闺女所嫁之地,我们列表比对可知,婚姻圈是传统乡间社交范围的标识,成就姻缘无论来自亲友还是媒妁,姻亲结缘范围基本限于40里范围之内。这一范围内,以男方所在村落为中心,形成远近不等的联姻圈,以10里为半径的区域为主要联姻地,无论平原还是丘陵山区村落,姻亲主要分布在这一区域;20里半径为第二圈层,分布在这一区域内的姻亲明显减少;20里以外联姻仅存在于少数家庭。
乡村振兴不是为了回到过去
记者:您从1985年开始持续进行中国古代农业地理领域的研究,您自己也说是孤独的研究者,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研究方向?
韩茂莉:当年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史念海先生要绘制中国历史地图,其中有农业这一部分,他就让我做宋代农业。宋朝是半壁河山,北边的辽金也都是我们今天的国土啊,于是就把辽金也做了。做完以后觉得我们这么一个农业大国,整体性的中国农业历史时期的研究,难道我们自己不做吗?我的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从史前时期一直到1949年以前。
我看了几千部方志,国内几乎所有与农业相关的考古遗址,特别是史前时期的,我都去过、很了解。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乡村社会地理还是比较有趣的。我的大部分研究内容是又累又枯燥的,要翻阅大量的典籍:古人怎么种地,怎么施肥,怎么积肥,这一茬庄稼跟下一茬庄稼怎么衔接,农时在什么时候等等。我带的研究生也没有做我这个研究方向的。这么几十年下来,我自认为是在中国活着的学者中掌握跟农业有关资料最多的一个人。我们高科技的问题玩不过国外,连自己本乡本土的这些基本问题都要看国外学者的著作,那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所以就坚持下来了。
记者:在您看来,应该怎样理解乡村振兴?
韩茂莉: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武汉,我们的生活水准、对于整个世界的认知程度,几乎和世界上发达国家最好的城市没有区别。但是我们有地区和城乡差别,乡村教育是中国的一个大事,教育是国民素质整体提高的关键因素。如果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缩小,乡村教育不能和城市到达同一个水平,对于中国整体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巨大的阻碍。
讲座中和读者交流时,提到传统乡村“死”去了,乡村振兴与城镇化是否矛盾等问题。传统农业社会土地对农民的束缚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中,创造更高的价值。乡村振兴和城镇化之间并不矛盾,当中国进入整体现代化进程,GDP提高的过程中,城市反馈给乡村,为乡村最缺少的硬件设施提供一个建设基础。比如说村村通、网络普及等,很多基础设施建设近年已经完成。
乡村振兴,不是回到传统乡村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而是将整个乡村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之中,教育、医疗、养老、卫生等各种保障,以及各种公共设施和服务,能达到和城市同一水准。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建立在国力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乡村振兴是国力发展的受益方,更是国家富强的参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