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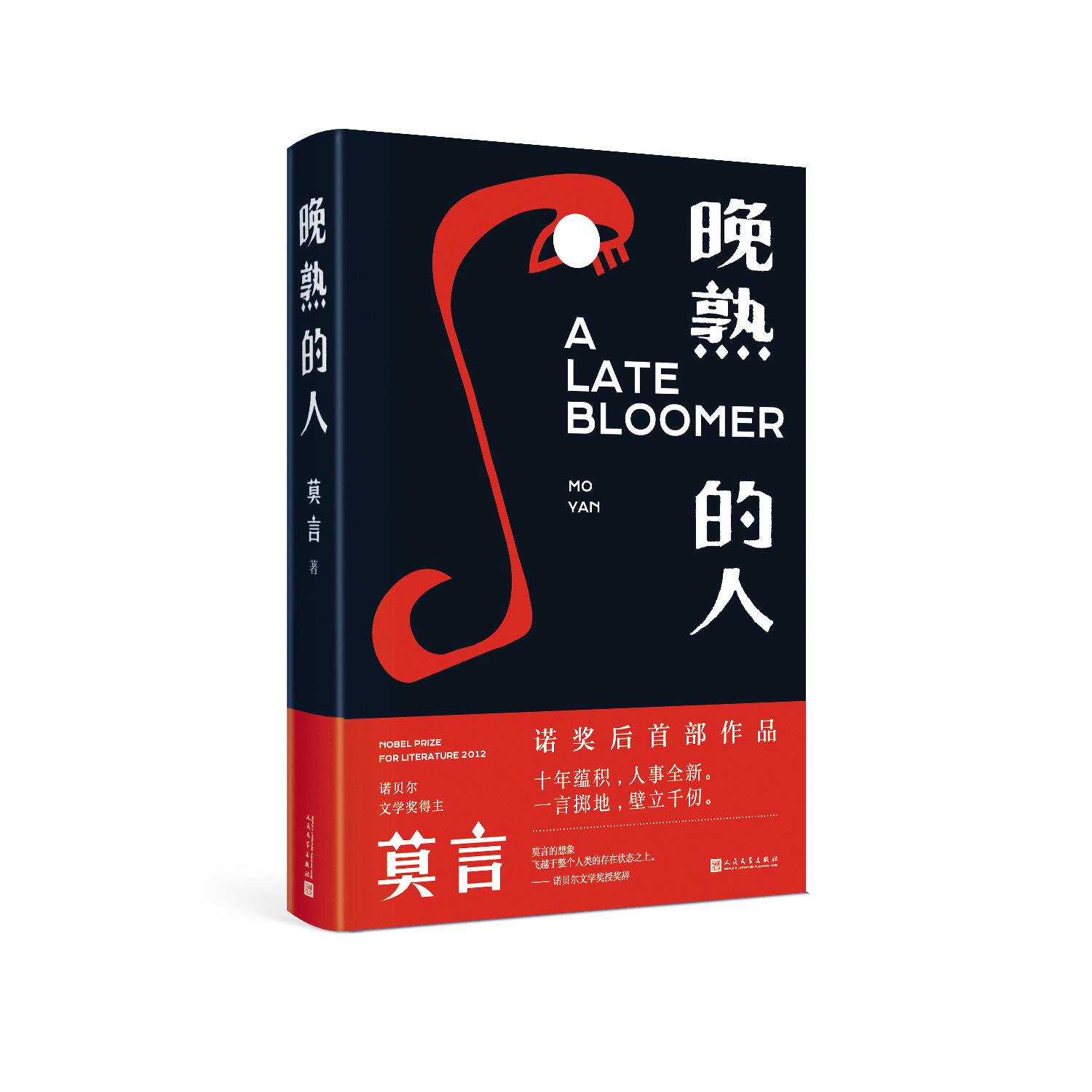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我风 通讯员 宋强
近日,莫言近作《晚熟的人》研讨会在莫言缺席的情况下在北京师大举行。会议由《文艺报》主编梁鸿鹰主持,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敬泽、潘凯雄、格非等参加。大家高谈雄辩,气氛欢快而热烈。
李敬泽:老莫不在,我们就自由了,直接面对作品
我们看《晚熟的人》,看到很多篇,实际上都有一个莫言回到家乡,回他那个高密东北乡。莫言回家乡,我们都知道,莫言从一开始就是站在高密东北乡的。但我觉得到《晚熟的人》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姿态有非常重要的变化。他以前的小说,家乡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回的地方,他是站在那里的,他是站在高密东北乡来讲话、讲故事、做出言说的。但是到了《晚熟的人》里面,可以说系统性的体现了一个姿态,他是从外面回去的。这也让我想起来,等于也回到了我们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非常根本的主题,就是鲁迅式的回乡的主题。其中《红唇绿嘴》开头很有意思,开头看上去很简单,说“乙亥岁尾,老父病重,我由京返乡陪护。”我看到这莫名想起鲁迅的《故乡》的开头,说“我在严寒中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不仅仅是在这一篇里,整个里边,某种程度讲都是在回到我们一个很根本的现代以来由鲁迅提出的那个“返乡”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个莫言和以前的那个莫言,之于他的“乡”,有了很不相同的意义。或者说作家的主题与他的“乡”之间的关系,和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很不相同的内涵。我觉得这是特别值得推敲,也特别有意思的。
过去站在高密东北乡里的那个莫言,曾经是一个对他的天地、对于他的世界尽在掌握的人,那样一个作家在红高粱中,在我们所熟悉的那些里,他对他的天地尽在掌握。但是现在回乡陪护的那个,在岁尾、在天寒的时候回到家乡的那个莫言,他对他的故乡,满怀着一种认识的、困惑的,探索、探求的,无法判断又努力做出判断的,非常复杂的一个情感,我觉得这本身非常有意思。
调过头来看,如果我们把老莫的回乡和鲁迅的回乡再比较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对于鲁迅来说那个相距两千余里、隔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几乎是被我们的现代所抛弃的一个宇宙的尽头,是一个停滞在那里的东西,这是鲁迅的那个回乡。而到了老莫这个回乡就非常有意思,这样一个人由京返乡,而这个“乡”不是一个停滞的东西,这个“乡”几乎是在老莫的图景里代表现实所有的庞杂的力量,缤纷、快速、变化、前进,这个“乡”变成了这样的对象。我觉得在这种比较中,或者说过去鲁迅的那个乡,几乎是一个历史的客体,是一个等待着历史去光顾的地方,历史老不光顾它,二十年不变的那么一个乡。而在我们此时此刻同样的另一个重要作家眼里,那个乡,几乎变成一个沸腾的历史的主体。我们的作家或者说小说中的那个“莫言”,是满怀着又困惑又好奇的去面对它,这个是极有意思的一件事。
潘凯雄:那个讲故事的人又回来了
回顾一下莫言的创作,他的成名作应该是1985《透明的红萝卜》,在《中国作家》发表,那样一种中篇小说、那样一种表达、那样一种意象,在1985年那个环境下面,那样一个背景下面,的确让人有点瞠目结舌。1986年《人民文学》上又来一个《红高粱》,这部作品大家比较熟,居然能这样写打鬼子。再往后1988年,第一部长篇《天堂蒜苔之歌》。两个中篇、一个长篇,这样一个莫言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坛横空出世,带给文坛的是一种什么?震撼、疑惑、吃惊、理解的、不理解的。
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那个时代,中国那个时候文学有另外一股力量,所谓先锋文学,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马原,我的印象中没有把莫言跟这一帮人搞到一堆,什么理由?莫言大一点?莫言比他们年长一点?其实莫言跟后面所谓先锋作家也就大概长了五岁左右,但是莫言在艺术表现上和这批先锋作家都有交集的地方,或者说都有重叠的地方,但是没有把他跟他们放在一起。
到了这个世纪以后,当我们发现当年的先锋,好像也不先锋了,那些讲故事的人都回来了,这次莫言新作出来我看到也有很大的标题说“那个讲故事的人又回来了”,其实莫言以前也在讲故事,只不过莫言今天讲故事的方式和过去讲故事的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在座的格非,在八十年代被称为叙事大师的、制造迷宫大师的,当时是青年作家,我们看他那时候的《迷舟》《褐色鸟群》,看的一头雾水,格非也差不多十年没有写作,去读博士做学问,一篇篇解读博尔赫斯,当他复出以后第一部长篇《人面桃花》,你发现格非也会讲故事,格非不玩圈套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是什么?这样一种巨大的变化和莫言的《晚熟的人》巨大的变化,我们把整个视线、整个观察问题的空间拉大拉长,其实这里就给我们不仅是对莫言个体的创作,其实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当下文学的研究和观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视角,也提供了某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这也是莫言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给我们提出的巨大课题。
格非:他的写作方法里面,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经过改造的传奇性
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大家觉得莫言现在慈眉善目,为人态度、跟人打交道,大家都觉得他非常慈祥。苏童曾经跟我说,老莫现在就是一个慈祥的长辈,感觉特别亲热。也有人说他的文章返璞归真。我的一个看法是,我说他回到的不叫“真”,他是回到了“诚”。
关于他的写作方法里面,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经过改造的传奇性。他一定意义上保留了这个传奇性,但是那个神人荒诞不经的故事、强烈的戏剧性情节遭到削弱,但是削弱归削弱,它还是影影绰绰构成强大的叙事动力,在作品里面莫言把他的主体还是保留下来,只不过他非常克制地运用这种传奇性和戏剧性。这也是他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感觉到特别朴实,特别可亲,点到为止,令人有的时候会想半天,比如说摩西最后去了什么地方,摩西最后怎么回事,他最后见到摩西的妻子,他们之间的对话,那个感觉上他保留了很多神秘性的内容。
另外,我认为他完成了记忆的重组。这个小说写的是现实吗?我觉得不见得,每个单篇的小说都有一个现实故事,但是大家如果仔细读的话会发现,每个故事周围弥漫着一个特殊的氛围,这个氛围是历史事件和记忆的碎片构成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单列的现实中的事件会勾连起莫言早年的小说里面一再出现的,那种对乡村的童年生活的记忆,他会强行的把这个记忆拉进来。我说强行可能不对,他做的非常自然,自然的进来。这样的话他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就是历史碎片跟现实的事件构成一种关系,氛围和主干之间构成一种关系。最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思考小说未来发展的一个方面,我觉得今天必须打破传统意义上那种僵硬的城乡对立的关系。很多人都在说乡村不能写了,现在要学会写城市。我觉得我们要打破这种观念,没人告诉我们说乡村不能写。莫言写了,写得很好。这当中你需要打破的恰恰是城乡观念的对立,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把握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存。